在矛盾交锋中“突围”
近年来,在一些军事热点地区,防空导弹与来袭空中兵器对抗激烈,各有胜负。“矛”利“盾”坚,对防空导弹来说,更多的“对抗”则是发生在战场之外。对更高、更快、更准的防空能力的追求,一直让各国角力不断、你追我赶。
近年来,美国一直在为“爱国者”防空系统赋能,使其能够正常的使用体量更小的PAC-3导弹,增强末段反导能力。俄罗斯于去年4月再次试射了新型反导导弹,该导弹甚至被一些西方媒体描述为“具有反卫星能力”。更多的国家也在跟进。以色列不断的提高“铁穹”系统及“塔米尔”拦截弹性能,韩国则制造和列装了“天弓2”防空导弹系统。今年11月,伊朗国防部也公布了巴瓦尔-373防空导弹系统的升级型,导弹射程显著增加。
那么,各国为何对防空导弹青睐有加?当前发展进程如何?今后朝哪些方向发展?请看解读。
防空导弹的作用有多大?从两场战事之中可窥一斑。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贝卡谷地之战,以色列空军的大编队机群攻击时,如入无人之境。原因主要在于,攻击前,以军已摧毁了叙利亚位于此处的19个“萨姆”-6防空导弹系统。
而在1973年的中东战争期间,借助同样的“萨姆”-6防空导弹,埃及和叙利亚曾击落以色列空军数十架战机,一度成为后者的“噩梦”。
一得一失、一胜一败之间,尽显防空导弹的地位、作用,也使其有了 “广袤长空的‘守门员’”之称誉。
从飞机投入战争的那一天起,防空就成了各国高度关注的课题。早期的战机飞行高度、速度有限,防空舞台上的主角是高射机枪、高炮。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战机性能的提升,防空导弹开始强势崛起并担当主力。
1944年,德国研制出了地空导弹“瀑布”,之后又在短时间内秘密研发“龙胆草”等多型陆基防空导弹。在此期间,美、英试制了“小兵”“助手”等海基防空导弹,进而拉开了导弹撑起“天网”框架时代的幕布。
自诞生以来,防空导弹在战火考验中持续不断的发展,现已有百余种型号。它们中既有可以直接扛在士兵肩上的单兵便携式导弹,也有由数十辆车载设备构成的高空远程防空导弹系统。
一般来说,防空导弹的主要构件有弹体、弹上制导装置、战斗部、动力装置以及气源、电源等。它的威力大小,不仅取决于导弹本身,还和总系统包括发射装置、目标搜索指示系统、地面制导系统、技术保障设备等息息相关。换句话说,负责探知目标的预警侦察系统、负责紧盯并辨识锁定目标的指示系统、负责指引导弹完成姿态调整的制导系统等共同组成了防空导弹打击目标的整个链条。
就防空导弹弹体本身而言,决定其性能高低的因素很多,如气动外形、发动机、导引头、引信研制水平等。以引信为例,飞行末段,引信会不断探测弹体与目标的距离,一旦足够近就引爆战斗部,随即产生大量破片打击目标。先进的引信可以将爆炸位置控制得比较精确,专门打击驾驶舱、油箱或发动机等要害部位,进而使防空导弹呈现出不同的战技术性能。
多年来,防空导弹的功能在不断拓展。如今,它们中有的能拦截来袭战斗机、直升机、无人机、巡航导弹、空地导弹,有的还能承担反导和反临近空间目标等任务,从而成了织就现代“天网”的重要支撑。
空袭之“矛”愈尖锐,防空之“盾”就愈坚厚。防空导弹在与空袭之“矛”斗法中不断“生长”,至今已经历了四代变化。
第一代防空导弹于20世纪50年代装备,大多数都用在拦截高空轰炸机和高空侦察机,如美国CIM-10A“波马克”、苏联SA-2等。第一代防空导弹体积非常庞大、稳定性差且基本上没有抗干扰能力,但它的出现使防空作战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其突然性和威力深刻影响了空袭样式、指挥策略、交战规模等。
在该代防空导弹压制下, 20世纪60年代,空中进攻开始转向低空和超低空突防。与此同时,更复杂的巡航导弹如BGM-109“战斧”出现。第二代防空导弹以拦截低空、超低空目标为主,强调快速反应,采用大量新技术新体制,在导弹推力、系统自动化、整体小型化和电子对抗能力等方面水平显著提升,如苏联SA-6、法国“响尾蛇”、美国“霍克”、英国“山猫”和“长剑”等都是如此。这一代防空导弹有的经历多次改型后目前仍在服役。
20世纪80年代,针对第一、二代防空导弹战术特征,特别是单目标通道的特点,空袭样式转变为在干扰机掩护下实施多波次、全高度、高密度的饱和攻击。为适应这一新变化,第三代防空导弹转向对高中低空和远中近程各类目标实施全方位拦截,强调抗干扰、抗饱和攻击、全空域拦截能力。该代防空导弹系统大都采用相控阵雷达和复合制导体制,同时高性能固体火箭发动机、计算机技术等得到普遍应用。比如,美国“爱国者-2”、俄罗斯9M96E、48N6E2等弹型。
20世纪90年代起,空中舞台“高、快、远、隐”各路新星“你未唱罢我登场”,第四代防空导弹随之诞生。该代导弹增大了射程,提高了制导控制精度和快速反应能力,还具备一定反隐身目标及防空反导一体化能力,可对大气高层和大气层外目标实施直接碰撞。其代表型号有俄罗斯S-400使用的40N6E和S-500使用的40N6M导弹、以色列“箭-3”导弹等。
进入21世纪,世界新军事变革迅猛发展,战争形态发生深刻嬗变,空天作战高度融合。这一严峻形势,倒逼着世界各国在防空导弹研发上不遗余力,呈现出如下特点:
不相同的型号同步研制。防空导弹在覆盖低、中、高空和近、中、远程方面各有优长。因此,不少国家通过同步研制不同型号和对其混编使用来扩大防护覆盖面。如美国通过“萨德”系统和“爱国者-3”导弹实施末段高低两层防御;俄罗斯S-300、S-400使用48N6、40N6型防空导弹等承担中远程防空,“山毛榉”系列导弹承担中低空、中近程防护,“铠甲”和“道尔”则承担末段防御任务。
族谱化、系列化发展。通过模块化、通用化、弹族化设计来增强防空导弹发展延续性和可扩展性,已成为不少国家的共识。这样,就能借助一次次“小步快跑”,来实现导弹性能的快速提升,适应新任务。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AMRAAM、ASTER、“标准”系列等。如“标准”系列,先后经历了“标准-2”“标准-3”“标准-6”等型号,弹径从始至终保持不变,共用一级发动机,主要是通过导引头与发动机等关键部位的更换或改良,来满足多种作战需求。
持续推进导弹组网作战。与空袭武器弹药的高机动性相比,防空导弹可防御的区域相对有限,因此各国一直在探索“互为手眼”的方法,寻求导弹组网作战。近年来,一些国家已开始着手发展防空导弹网络化作战统一制导体制、互操作系统、高精度雷达组网技术等,其目的是将不一样的区域的防空导弹系统连接成一张网,借助算法优选出更合理的拦截方案,用处于最佳位置的防空导弹来实施拦截。
向“天”向“快”寻求新能力。近年来,一些国家开始将防空导弹所打击目标扩展至空天侦察手段、临近空间飞行器、高超声速武器等新型威胁。2021年,以色列和美国宣布合作研制“箭-4”导弹以应对新型远程导弹和高超声速武器;俄罗斯将服役的S-500和正在研制的S-550,据称都将装备77N6-N、77N6-N1导弹,可以拦截高超声速飞行器甚至太空目标。
打造灵动之“镖”快速补位。针对无人机、巡飞弹等“新生代势力”带来的近程低空威胁,防空导弹也在以变制变,呈现出低成本、高精度、强火力等新趋势。如以色列“铁穹”系统能以卡车和拖车为“坐骑”,部署灵活,在面对火箭弹攻击时,可在短时间内预判弹着点,自动计算拦截可行性并实施拦截。便携式防空导弹也在因时而变,如美国“毒刺”、英国“星光”、俄罗斯“雷霆”等,几乎可“傻瓜式”操作,能对低空、超低空飞行的战斗机、直升机和无人机造成更大威胁。
进攻与防御是战场上一对永恒的矛盾,在彼此制约的同时又促进了相互的飞跃式发展。在体系化对抗增强、新威胁纷至、作战形态发生根本性变革等新情况下,未来的防空导弹或将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发力:
提升在复杂战场环境中作战能力。防空导弹今后将面临高超声速打击武器、新型隐身战斗机、隐身无人侦察机、智能察打一体无人机等多种 “对手”的挑战,加上防区外精确攻击、远程强渗透攻击、蜂群式无人化智能打击等新攻击形式的出现,防空导弹将不得已在适应复杂战场环境方面再进一步,如提升反应速度、增强抗毁性和抗复杂电磁干扰能力等。
进一步一体化、通用化。一体化既指对防空导弹弹载设备做一体化设计,使导弹在“瘦身”同时搭载更多有效载荷,也指对发射装置进行一体化设计,使多种类型的防空导弹可“共享”一种发射装置,大幅度的提高发射效率。通用化,则指实现军种间通用和导弹部件通用,改变弹族种类非常之多的局面。如俄罗斯S-300实现了海、陆、空三军通用;以色列的“铁穹”系统新近推出了舰载版等。
借助智能化和多能化提升抗击效力。在智能决策方面,防空导弹或将实现目标自动识别,并具备目标切换、动态规避等功能;在体系贡献度方面,未来防空导弹还可能被赋能用作探测器,获取最前沿信息回传后方,或作为运载平台将多枚子弹药“快递”至预定空域;在多目标打击能力方面,未来防空导弹或将实现多类目标智能应变打击、跨介质追击目标等;在协同方面,防空导弹或将利用互联网联通“组团”作战,在多套防空系统数据支援、接力制导下,实现多枚导弹协同攻击目标。
图①:可由S-300F及S-400防空导弹系统发射的48H6E防空导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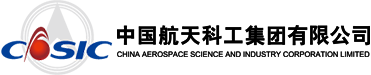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官方微博
 官方抖音
官方抖音
